美國人血液中的保守主義:
連革命都是保守的
約翰·米克爾思韋特
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
選自《右派國家》
美國保守主義運動的時間相對較短,而美國例外的保守主義則要回溯到美國誕生之初。一直以來,美國就具有保守主義的天性——對國家權力的懷疑、對商業的熱情以及篤信宗教。美國在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對自己那種與生俱來的保守主義感覺良好,以至於不需要發起一場保守主義運動來表明它的原則或使敵人煩躁不安。
美國的血液中浸透著保守主義思想,這或許會使某些人產生一種奇怪的感覺。美國難道不是由啟蒙運動催生的國家嗎?它難道不是世界上第一個「新的國家」嗎?它不正好是一個年輕國家的樣板嗎?難道它不是「激進派的烏托邦和保守派的巴別塔」嗎?美國深思熟慮地掃除了舊世界的君主政治、貴族統治和國家教會,並保障人民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個新共和國在誕生之初的幾十年里站在革命的法國一邊,反抗舊世界那些沆瀣一氣的大國。事實上,當法國的革命者猛攻象徵古代專制主義和壓迫的巴士底獄的時候,法國將軍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將巴士底獄的鑰匙送給了喬治·華盛頓。
毫無疑問,美國的保守主義是一種例外的保守主義——一種具有前瞻性的商業共和國保守主義,而非老歐洲反動的托利主義。即便如此,它還是屬於保守主義。美國是個年輕的國家,但它也是一個正在走下坡路的年輕國家;美國是革命的產物,而這場革命也不同於法國的革命。建國伊始,美國社會中就存在一些因素——包括宗教狂熱和資本主義因素,甚至還包括地理因素——能阻止任何滑向左傾的可能性。美國是世界上唯一從未有過左派政府的發達國家。
歲月雖經年,心依舊年輕
我們先從美國不再被認為是一個真正「年輕」的國家這一看法開始討論。最早的定居者來到這片土地的時候,詹姆斯一世還在王位上,而英格蘭也還未變成不列顛。在查理一世被處死之前,創立於1636年的哈佛大學向伽利略提供了一個教席。在德國和義大利(被認為是老歐洲的一部分)統一前100年,《獨立宣言》就已經簽署了。波士頓和華盛頓的歷史中心給人感覺同許多歐洲的都城一樣悠久(在某種程度上說,甚至還要更悠久,因為它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並未遭受轟炸)。在滿懷羨慕的美國人心目中,許多把不列顛界定為一個古老國家的傳統——如帝國的盛況和命運、查爾斯·狄更斯的聖誕禮儀、夏洛克·福爾摩斯的獵鹿帽——都是在美國的憲法成文一個世紀之後出現的。奧斯卡·王爾德一個世紀之前就曾一語雙關地說道:「美國的青春是其最古老的傳統,它到今天已經歷時300年了。」
美國擁有最古老的憲政制度,就這一點而言,美國有足夠的理由說自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美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國,擁有最古老的民主和聯邦制。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成文憲法(1787年),民主黨有足夠的理由說自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黨。1789年以來,法國歷經了5個共和國,更不用說其間還有君主制、帝國、五人執政團、執政官和通敵賣國的法西斯獨裁統治。英國新工黨徹底修改了英國立憲政體中最古老的組成部分之一的上議院。但是美國只對它的憲政安排稍稍做了一點修補,如讓選民而不再是州立法機構來選舉聯邦參議員。即便是廢除奴隸制的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目的也是迫使美國實踐其憲法中最初的理想,而不是要背離那些理想。
在今天的生活中,人們永遠可以感覺到過去的存在。美國人總是根據那一群身穿及膝短褲、頭戴撲粉假髮的紳士的設計來做重大決定,如婦女能否墮胎或孩子是否要在學校祈禱。政治家很樂意把自己說成是傑斐遜派和漢密爾頓派,即便是網路自由意志論者——很難說他們是最關心歷史的人——也把自己描述為「帶筆記本電腦的傑斐遜派」。除內戰後為解決所有美國人平等問題的修正案外,美國憲法與當時開國者的想法非常一致——建立一種複雜的制衡制度,以防止未來出現一個喬治三世。美國歷史學家丹尼爾·J.布爾斯廷(Daniel J.Boorstin)在1953年回望歷史時評述道:「即便違背我們的意志,歷史也使我們適合去理解保守主義的含義,我們已經成為歷史連續性的榜樣,成為使成就與過去連接在一起的榜樣,這些成就源於使制度能夠適合某一特定的時代和某個特定的地方。」
確實,美國過去的歷史曾被19世紀最血腥的衝突內戰中斷。但美國內戰在許多方面卻非常保守。雙方都大聲宣稱自己是在保衛憲法。北方捍衛的是聯邦制,後來捍衛作為憲法靈魂的個人平等的觀點;南方捍衛的則是同一部憲法所保證的州權。美國異乎尋常地避免了歐洲常見的那一類掃除舊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命戰爭。
美國人緊緊抓住歷史和傳統不放的一個原因是他們不像德國人或日本人,不必埋葬自己的過去。他們精力充沛地慶祝陣亡將士紀念日和美國獨立日,定期使有關建國之父的書籍攀上暢銷書榜的榜首,建立歷史協會來重現美國內戰,成群結隊忠貞不渝地來到那些偉大的紀念碑前。國會山上總是有很多學童,到這裡來接受對美國憲法表示敬意的教育。(要是一位義大利教師如此崇敬地說到義大利的憲法,那是無法想像的。)美國最受歡迎的一檔兒童電視節目是《自由之子》(Liberty』s Kids),它反覆向孩子們親切講述美國革命的英雄事迹。
但是由於美國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新的國家,因此認為根本沒有必要像英國和法國那樣狂熱地推陳出新。他們沒有用氣勢逼人的新建築來損毀華盛頓的舊貌,就像現代主義者感覺需要使倫敦翻新一樣。歐洲的許多地方給人的印象分成兩派:「舊派」懷疑一切新的東西,目前在英國正快速上升的「新派」則痛恨舊世界,並且認為新奇事物本身就是優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老歐洲現正投身於創造一個新歐洲的激進實驗中。《馬斯特里赫特條約》(Maastricht Treaty)尚未長大成為少年,共同貨幣才剛走出襁褓,一部新憲法正處於辯論之中,2004年有10個新成員入盟,人們的話題是創建共同外交政策。在美國,除了一部分激進的邊緣人群以外,所有人都對美國的憲政安排感到滿意。
一場保守主義革命
美國這場革命有多保守?一開始,我們必須承認,那顯然是一場革命。就像戈登·伍德(Gordon Wood)在他1993年的《美國革命的激進主義》(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一書中表明的那樣,反叛者不僅趕走了英國人,也根除了那些封建社會秩序的法律標誌——長子繼承權、限定繼承權、貴族稱號、國教,等等。他們把自己的共和國建立在兩個原則基礎之上:第一,人人生來平等;第二,權力最終來自「人民」的意志。
然而,革命者所做的一切都含有保守主義的潛台詞。革命首先是作為殖民地的反叛開始的,而不是像他們的法國同儕那樣,企圖改造出一個全新的世界。革命工作是由擁有土地的鄉紳而非由離群索居的知識分子或怒火中燒的農民來進行的。這些人機智穩重、事業成功,他們起初認為自己是在為英國憲法的原則而戰,而不是在反對這些原則。他們沿用歷史上英國政黨的名字,自稱為「輝格黨人」,而將對手稱為「托利黨人」,並宣稱自己是在保護舊有的英國的權利(例如陪審審理、法律上的正當程序、自由集會以及沒有提議不得徵稅),而非為確立新的權利而戰。
革命的結果是相當克制的。美國托利黨人最糟糕的結局只是遭流放和被驅逐而已。在費城,並沒有發生像巴黎那樣的公審和死刑判決。相反,革命引發的是一股制憲的高潮。緊隨1776年的《獨立宣言》,每個州都草擬了自己的憲法,而且1783年的《邦聯條款》將各州有限地結合到了一起。各州隨後於1787年齊聚費城,起草一部在一定程度上協調中央控制與各州舊有權利之間關係的全國性憲法。美國的開國元勛在平靜的舊時代里開始凝思自己要做的事情。
毫無疑問,美國革命捍衛的不僅僅是古代英國的自由。開國元勛們逐漸認識到,他們需要更具創造性,而不僅僅是捍衛現狀。就像約翰·傑伊(John Jay)宣稱的那樣,他們是「第一批受到上天恩寵的人,有機會審議並選擇自己在其中生活的政府形式」。而且,相對於捍衛古代英國憲法中的權利,他們對保證普遍的自由更感興趣。他們不僅閱讀洛克和孟德斯鳩的著作,也閱讀威廉·布萊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的作品。不過他們追求的是一種相當溫和的自由,即個人儘可能地不受政府的干預而追求自己的目標。正是由於這種對公民自由壓倒一切的承諾,才使得美國革命具有保守主義的優勢。它限制了政府的野心,政府的好壞不是根據其提高道德或促進繁榮的能力來判斷,而是由其讓人民自由自在地追求個人目標的能力來決定的。美國的開國之父與正直的貴族精英思想沒有瓜葛,但是他們對大眾先天的善良也不抱幻想。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人文集》(Federalist)第51篇中寫道:「政府不是必要的……如果是由天使統治人間,那麼對政府的內外約束就沒有必要。」
本著這種精神,美國的開國之父把民主看作是達到更高目標的手段,而不是把民主本身當作目的,而更高的目標是自由。他們小心翼翼地設計了一種制度,以防止民主陷於「混亂和荒唐」之中。他們使用分權來防止民主最常見的危險——多數人壓迫少數人、少數人綁架政府、民選代表把自己的利益凌駕於人民之上。他們建立了參議院,議員起初是由各州任命而非直接選舉產生,以便「為大眾的情緒波動提供一個穩定器」。他們利用聯邦主義原則,以確保決策儘可能在最低層級進行。當然,他們關於「人民」由哪些人組成的思想有點局限。例如,婦女、無土地者和奴隸無權投票。開國者們錯綜複雜的設計令人注目。參議員任期6年,從而具有更長遠的眼光;眾議員任期2年,從而與人民的意志更接近;總統由選舉人團而不是由原始的多數來選舉,從而確保了總統關心小州的利益。
英國保守主義的守護神埃德蒙?伯克對美國革命的崇敬之情同他對法國革命的仇恨程度一樣深,這不足為奇。他認為,法國革命的結局是個災難,因為他們是為抽象的自由而戰(如伯克所指出的那樣,是為「自由的噴發」而戰),也因為他們要利用政府來改造人性。美國革命是成功的,因為他們是在為人們的真正自由而戰,為美國固有的生活方式而戰,以反對不斷加劇的權力專斷野心。他們調和政府以適應人性,政府的職責是要保護個人追求自己的幸福,他們從未對此視而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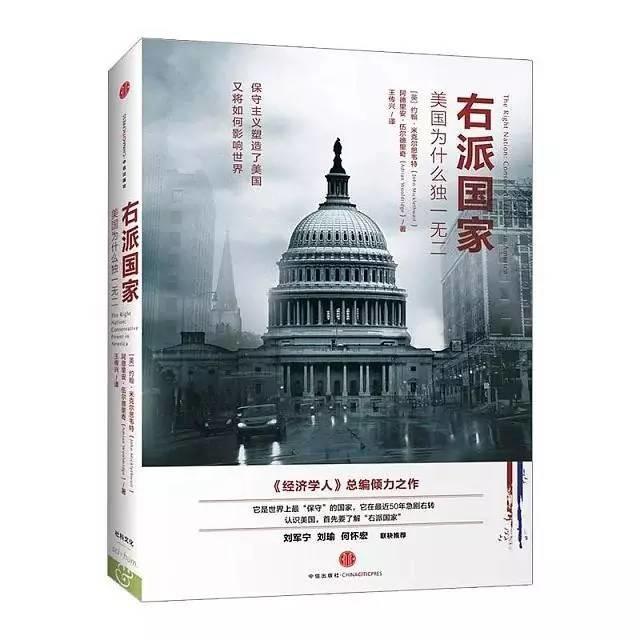
請您繼續閱讀更多來自 哲學園 的精彩文章:
※程東金:「特朗普現象」與美國的保守主義政治
※丘成桐:數學和中國文學的比較
※市場究竟是不是理性的?諾獎得主如是說
※當希拉里和特朗普還是朋友
